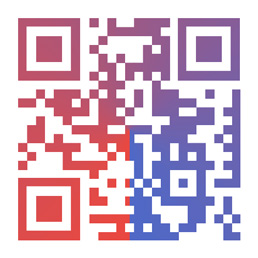A股步入牛市的呼声渐高,乐坏了投资者,也急坏了投资者。
8月14日,齐鲁转债(113065)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齐鲁银行于2022年发行的80亿元转债有79.93亿元实现转股。截至8月20日,已有齐鲁转债、成银转债、苏行转债、杭银转债、南银转债、中信转债等六只银行转债到期摘牌,与年初存续的13只银行转债相比,可转债市场银行标的仅剩7只,银行转债余额也缩水至425亿元。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可转债市场共有57只标的到期、强赎退市,总退出规模超过1000亿元(包括到期、强赎、回售以及转股)。但今年以来新发转债数量有20只,总规模仅245.77亿元,市场发行与退出的倒挂引发投资人极大关注。
“规模高达350亿元的浦银转债也将于10月28日到期退市,届时转债市场中银行品种规模将缩减至900亿元以内,行业权重占比将由目前的22%左右下降至14%,供需矛盾空前突出。”8月19日,上海澜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佳莹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而对机构投资人而言,当前资金可能向两类标的分流:一是中小规模成长债,如新能源、AI 概念转债,弹性大但波动高;二是低估值蓝筹债,如公用事业、消费板块转债,承接防御性配置需求。
银行转债掀起“退出潮”
由于银行股今年表现较好,正股股价飙升后多只银行转债触发了强赎条款,银行转债今年掀起“退出潮”。因此,原本超8000亿元转债市场规模也急剧降至7000亿元以下,新债发行的速度赶不上老债退出的速度,市场上的投资者变成了“缺水的鱼”。
“尽管转债强赎潮暂歇,但银行转债促转股诉求较强,促转股将加速银行转债的缩水,在最激进的情况下,年末或仅剩下两只银行转债。”8月20日,江苏飞马私募投资合伙人杨贤告诉本报记者。
更直观的数据显示,当前银行转债的余额已从年初1910亿元缩水至1250亿元。
财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孙彬彬团队最新发布的研报显示:“常银、上银转债转换价值均超115元,兴业、重银、浦发转债转换价值超100元。若保守估算,年末或剩余兴业、重银、青农、紫银4只转债;若激进估算,假设兴业、重银能够完成债转股,年末或仅剩余青农、紫银两只银行转债。”
许佳莹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在银行转债规模下降的背景下,此前依赖银行转债做底仓的机构投资者,不得不调整策略。
“一方面,机构对其他高评级转债的配置需求可能会上升;另一方面,一些中小规模但行业前景良好的转债也可能进入基金的视野,如一些新兴产业中的优质企业发行的转债,虽然波动可能较大,但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符合部分基金在追求稳健的同时兼顾收益增长的需求。总的来说,如何重新选择标的,调整持仓权重占比,是机构投资者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许佳莹坦言。
上海一家公募基金固收团队分析师认为,银行发行可转债用以补充资本,但最终都是奔着债转股的目的而去。特别是对于即将到期的转债,如果到期后大量投资者不愿转股,银行就需要支付大量本息。因此发行人会想尽办法促使转债转股,而促转股进一步加速银行转债余额的缩水。
事实上,随着转债市场银行标的减少,也有市场观点认为我国阶段性的化债目标已经完成。对此,许佳莹表示,从积极一面来看,银行转债的大规模退出确实反映了我国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但是将转债市场萎缩简单等同于化债目标完成阶段性任务,这种看法存在片面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和银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商业银行通过可转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紧迫性确实有所下降。这种变化与监管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管理更加精细化,鼓励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工具来优化资本结构。这种政策导向的变化,使得银行在选择资本补充工具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不再过度依赖可转债这一单一工具。另外可转债市场的规模变化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除了政策因素外,还包括市场利率环境、投资者风险偏好、发行人融资需求等多重因素。当前转债市场的萎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不能完全归因于化债进程。”许佳莹表示。
机构投资人急调策略
在当前新债发行速度和规模都无法填补银行转债的空缺下,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该如何化解?
“从投资策略来看,传统策略可能需要进行调整。过去银行转债因其低波动性和较高票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标配,现在则需要更加主动地寻找替代品种。公用事业类转债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这类品种同样具有低波动特性,且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例如电力、水务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发行的转债,可以作为新的底仓品种。”前述公募基金固收分析师表示。
在许佳莹看来,在增量新债短期无法填补银行转债留下的空缺之下,机构投资者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存量债中找好标的,而此种策略,可能引发与A股共振的可转债牛市。
许佳莹指出:“除了前面提到的公用事业板块外,部分现金流稳定的消费类企业也值得关注。这些企业的转债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较高。另外,一些大型央企发行的转债也具有类似特性,这些企业通常信用资质较好,违约风险低。另外市场也需要培育新的供给来源,目前来看,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行业的可转债正在快速成长。这些行业的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成长性,虽然波动性相对较大,但能够提供更好的收益弹性。长期来看这可能是可转债市场走向更加多元化、成熟化的重要契机,市场参与各方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应对这一变化,共同推动市场的健康发展。”
那么,可转债“牛市”是否已经到来?许佳莹认为,供给收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高了存量转债的估值水平,由于可投资标的减少,资金被迫集中配置于剩余品种,估值自然上升。估值提升对持仓投资者形成明显利好,特别是对那些持有优质个券的投资者而言,可以获得可观的估值溢价收益。
“但是供应偏紧也带来显著投资挑战。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配置难度加大,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固收+’产品面临优质底仓资产短缺的困境。以往银行转债因其低波动、高信用特性成为理想的配置标的,现在则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寻找替代品种,这无疑提高了投资管理成本。综合来看,供应偏紧对投资者的影响不能简单用利好或利空来概括。理性投资者应当客观认识当前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调整投资策略,重点关注估值相对合理、基本面扎实的品种,避免盲目追逐高溢价个券。”许佳莹提醒道。
上海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业务部负责人刘刚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中证转债指数自2024年四季度低点以来累计涨幅已达32%,已经符合技术性牛市的定义标准,市场日均成交额较2023年同期增长约40%,显示资金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在正股市场带动下,转债市场出现普涨格局,超过80%的个券实现正收益,其中新能源、半导体等赛道类转债平均涨幅更达到35%以上,赚钱效应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