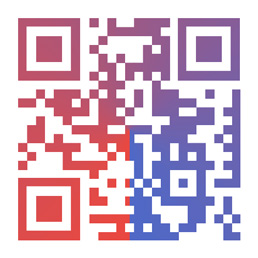7月21日, 江西浮梁县融媒体平台上一篇《北斗昭明——浮梁北斗书院兴衰考》如投石激浪,不到两天竟掀起23万的点击巨浪!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其背后,又潜藏着何等深沉的文化渴念?这岂止是文章的成功?分明是浮梁人对历史文脉的深情回眸,是时代对健康文化根脉的殷切呼唤。
江西是个好地方,浮梁曾是孕育了景德镇的母县,其“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誉驰名中外。28万人口小县,浮梁历史上经济富庶,陶瓷文化星光灿烂,文化名流辈出,尤其近代史上,浮梁浮北乡村重文兴教,商业文明拔助的文化自建,培养了一批批文化俊才,这些出自乡野的文化传承人,犹如惊鸿一瞥点亮乡土,更为近代地方文化兴衰留下了闪亮的光芒!
如今,在喧嚣尘世之中,人们的心灵深处那份渴求从未消失。基于浮梁历史的灿烂文化,浮梁人张干明、钱锋先生倡议成立北斗文化研究会,张树安研究员以心血梳理北斗书院兴衰脉络,恰如为焦渴的田野引来大小北河一渠清流。其在筹备会上的一篇发言稿,经浮梁融媒体平台转发后,两天的点击量就突破了23万次,这一炸裂现象的背后,实则是23万颗心灵在文化荒漠中自发寻找清泉的集体回响——我们灵魂深处始终渴望着那些能滋养根脉、照亮心灵的文化甘霖!
张树安研究员曾是我中学老师,也曾担任浮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他不仅是我的先生和人生导师,也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干部之一。张树安老师退休后一直执迷于种菜,更热衷于地方文化的挖掘与探寻,并且乐于其中乐此不疲。
他笔下的北斗书院,其名即如指路星辰,其史更如精神灯塔。张树安先生深入考掘书院兴衰,正是重新点燃这座文化灯塔的壮举。书院当年培育英才,如北斗引航,辉耀一方文脉;今日考证其史,亦如擦亮尘封的明珠,让历史智慧重新照见浮梁前路。这岂是寻常考证?分明是让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光,重新映照浮梁大地的崭新航程!
当23万次点击汇聚成流,这已不是一次普通的阅读行为,而是浮梁儿女一次深沉的文化自省。它昭明:唯有那些真正蕴含历史底蕴、承载精神高度、指引向上之路的文化活动,才能在时代洪流中牢牢扎根,并唤醒民众心底最深沉的认同。浮梁这场北斗文化研究热潮,恰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乡村振兴之文化振兴最本真的动力:它源于民众内心自发,也必将植根于民众心底!
23万次点击量,岂止数字?那是23万颗心朝向北斗的仰望,20万双手对文化根脉的深情触摸。张树安先生笔下北斗书院的光芒,岂止属于历史?它正穿越时空,辉映今日浮梁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愿这束北斗之光,永不黯淡!它必将点燃更多地方文化薪火,于神州大地上熊熊燃烧,点亮更多心灵深处不灭的星辰。 作者系原《浙江日报》资深记者 吴中平
附张树安先生的作品:
北斗昭明——浮梁北斗书院兴衰考
张树安
2025-07-21 17:0923万+阅读 文苑
浮梁北乡,人杰地灵!大小北河,孕育了浮梁北乡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回望历史,浮梁北乡的书院、书堂、私塾,曾如繁星般点缀其间,照亮了无数求索的心灵。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岁月的风霜无情地侵蚀着过往的记忆。曾经灿若星河的文化印记,连同我们心中那最后的守望与阵地——北斗书院,许多珍贵的情节都已悄然湮灭在时光的尘埃里,留给我们的,唯有那些令人扼腕叹息的、零落的记忆碎片。即便是离我们年代最近的北斗书院,其辉煌过往,也早已不为今人所熟知。
北斗书院,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虽初创倡导者何人,初创具体何年,因史料缺失,我们暂未确考,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诞生之初的宏大气象!彼时,千年古县浮梁按方位分设东南西北四大书院。而我们习惯所称的“北乡”,涵盖蛟潭以北的峙滩、储田、经公桥、西湖、勒功、江村和兴田。承载着北乡文脉与希望的北斗书院,雄踞于北乡的中心腹地沽演下村——即今沽演粮站一带。令人怅惘的是,现代公路穿院址而过,只余下院址上部分残垣断壁、缩小的水塘和一块残碑在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荣光。
北斗书院是什么样子,今人没有见过。幸得曾在北斗书院求学、后在储田中学当过老师和景德镇工作的江村郑惟馨老人,留下的一篇回忆文章《北斗书院》,为我们描绘了这座文化殿堂的壮丽图景:
“北斗书院,坐北朝南,气象庄严!迎面便是一座雄伟的门楼,其上‘北斗书院’四个大字,横贯苍穹,气度非凡。门楼两侧,各砌有约六米高的方砖墙,通体以石灰粉刷,洁白如雪,呈‘八’字形傲然撇开。门前,一片宽阔的绿茵如毯,静候着求学的脚步。步入其中,但见布局精妙,处处讲究对称之美。其建筑规模宏大,空间异常宽敞,整整一百间房室,鳞次栉比,皆为两层楼房。内设会议厅、工作室、仓库、教室,功能齐备。穿过正门,两侧楼房间,豁然开朗处是一个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池沼如镜,花圃溢彩。池沼周边,垂柳依依,随风摇曳;空地与花圃旁,松柏苍翠,翠竹挺拔,各色花草点缀其间,生机盎然。书院最深处,一座魁星楼阁拔地而起,直指云霄!其楼阁顶端,四角飞檐翘起,气势磅礴。登临绝顶,极目远眺,方圆数里,尽收眼底,令人胸襟为之开阔!”
据目前掌握的文字记载,北斗书院早期的山长,是溠口的朱之翰先生——他也是后来山长朱帮道(朱大绶)先生的祖父。朱之翰乃清末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北乡文化界和文人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与尊崇。须知,书院山长一职,绝非等闲之辈可胜任!必得由全北乡的文人学士共同推举,候选人不仅需有高深的学养功名,更需具备令人信服的崇高威望。
书院的架构是这样的,设山长一人,财务一人,杂役、巡察(负责山长和书院保护,到各地巡察催送田租)若干人。为何这里没有教书先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可能令人稍感费解:北斗书院自身从未直接开办过官办学校或常规教学。虽然它曾办过几期经学(即私塾),但这与书院的主体功能是分开的。简言之,书院本身“兴教而不教学”。这需从古代书院的性质说起:我国传统书院,大致肩负着六大神圣使命:
其一,教育教学,设经学讲堂培养生员;其二,管理地方教育,选拔人才,其职能颇似今日的教育局;其三,学术研究、交流与传承,乃思想激荡的殿堂;其四,社会教化与时政监督,担当一方文脉的守护者;其五,图书资料的贮藏,犹如古代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其六,文庙祭祀功能。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往往六者兼备。而我们的北斗书院,则简单些——它并不独立承担常规的办学之责。书院虽拥有教室、房间、课桌板凳等完备设施,但主要延请地方上享有盛名的教书先生前来开堂授课。书院无偿提供教室和教学用具,却并不支付先生薪金。先生的收入,全凭其学识魅力吸引学生缴纳学费。先生学问越精深,慕名而来的学子便越多,其收入自然丰厚,培养出的人才也更显卓越;反之,则难免门庭冷落。清末的朱之翰先生便是极负盛名的典范。
及至民国,科举废除,老学究渐失市场,新学之风日盛。此时,江村的郑伦元先生,既是山长,也是教书先生。他身为留日归来的海归学子,学识新锐,备受推崇。撰写北斗书院回忆的郑惟馨先生,以及江村的郑振球先生等,都曾师从郑伦元,并引以为毕生的荣耀!
民国时期,继朱之翰先生之后执掌北斗书院的,有其子朱舫良先生、其孙朱大绶先生。朱大绶先生升任国民党浮梁县党部书记长后,则由朱大来先生继任山长。江村的郑景尧先生,是沽演北斗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
值得铭记的是,北斗书院除山长外,还设有校董会。陆续有十多位校董,如严台的江资甫先生、流口的张佩贤先生、后来还有梅湖的姚以南先生等十多位地方权贵贤达,都曾担任过书院校董,为书院发展倾注心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前文一直沿用“山长”之称谓。然而,到了北伐战争之后,北斗书院的主事人,其称谓已悄然变化——不再称“山长”,而是改称“团总”!不知其他地域的书院在民国时是否也如此称呼,但北斗书院确是如此。这“团总”之名,本是地方武装民团长官的设置。自朱之翰山长延续至民国,称谓便开始转为团总,此后皆循此例。这称谓的转变,或许正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烙印——军阀混战,割据一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往往意味着话语权。用团总之名或有用枪杆子护卫笔竿子之意。
当时的北斗书院,虽非北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但绝对是北乡最具权威、最有话语权的地方!书院每年会召集一两次集会(实为校董会),由团总负责总召集。会议内容绝非寻常,它关乎北乡公益事业的新建与重修,更肩负着调解全乡各村乃至个人之间复杂的山田纠纷的重任。因为乡民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朴素的信念:有了纷争,就要去找当地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人来主持公道。北斗书院,正是这样一个汇聚了北乡顶尖文人与所有权贵精英的神圣殿堂!例如,校董张佩贤先生曾任六区(江村区)区长,姚以南先生后曾任五区(峙滩)区长,朱大绶先生更是官至浮梁县党部书记长。
书院自身拥有良田千亩的雄厚产业,其收入除维持书院日常运转外,更有一项惠及北乡的善举——资助北乡优秀学子外出深造!尤为关键的是,书院团总手下,掌握着十几条枪。在乱世之中,这便象征着绝对的权威与话语权!这些枪,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岁月里,无疑是个惹人垂涎的“好东西”。那时,红色政权已在北乡大部分地区星火燎原,流口、儒林、柏林、溠口等地,皆是共产党人活跃的区域;而石溪以北,则是白区的顽固堡垒。红区白区,对这十几条枪无不“心仪不已”。甚至邻近的祁门高塘,也组织起义勇队,三番五次深入北乡“围剿”红军。
历史的悲剧,在1934年农历八月二十三那个夜晚骤然降临!高塘义勇队从勒功翻山,直扑溠口,未遇红军,竟悍然洗劫溠口,焚烧三幢民房!随后,这群匪徒绕道到沽演,将魔爪伸向了北斗书院——他们不仅劫掠了书院的珍贵财物,更夺走了所有枪支!为了掩盖罪行,便于逃窜,这群文化刽子手竟丧心病狂地纵起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烈焰吞噬着这座承载着北乡文脉的殿堂!那一刻,书院的教工、学子、当地村民以及大刀会志士,无不悲愤填膺,他们不顾一切地全力追杀高塘劫匪,沿河一路追击至下黄,可惜最终失去了匪徒的踪迹。劫匪们则经石溪转沧溪,从白毛仓皇逃回了高塘。
创办仅五十余载,凝聚着北乡无数心血的北斗书院沽演校园,就这样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这是北乡文化史上一次惨痛的浩劫!
书院剩余的田产,由朱大绶先生主持,按北乡的乐农、桃墅、全民、新政、兴田、峙滩六所中心小学平均分配,其收益仍用于兴办教育,延续着书院的文教薪火。而那些曾为书院呕心沥血的校董们,也依然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教育事业。朱大绶先生回到溠口创办乐农初级中学;张佩贤先生则在流口,利用宗祠承恩堂办起了国民学校(张有帮、张纳容等曾在此求学);姚以南也在梅湖兴办学校(据说至今健在的陶学渊先生曾在该校执教)。
三年后的1937年,张佩贤先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重振北斗书院的强音!原来,自民国九年开始,张佩坚先生便在中渡口购置大片土地,兴建了一片坐北朝南、阳光普照的门面房,取名“朝阳巷”,门楼高悬“朝阳门”匾额,房屋用于出租。1937年,张佩贤先生力主在朝阳巷21号重办北乡公所与北斗书院,并亲自担任山长。原北斗书院的学东们,绝大多数都参与进来。此时的北乡公所,成为北乡人士议事决策之所;而朝阳巷的北斗书院,则化身为北乡学子前往景德镇求学或经景德镇外出深造时,一个温暖的落脚点与精神驿站。
这座承载着流离文脉的景德镇朝阳巷北斗书院,伴随着景德镇的解放,因时代变迁及原校董的命运转折,最终于建国前废止。从沽演初创到朝阳巷落幕,北斗书院存续凡七十余载,其命运跌宕,令人唏嘘!
北斗书院,曾走出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目前所知,仅仅今江村乡一个乡,就有三个学子,走进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他们是“共和国不会忘记的烈士”、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的大英雄江式训,曾经著述出《抗战必胜论》的国民党少将朱云影,中国民主建国会34个创党元老之一的林涤非。可以肯定,建国初期北乡许多有文化的干部、教师,多从北斗书院走出。
去年,惊闻承载着北斗书院最后记忆的景德镇老城区的朝阳巷,将被陶文旅开发的消息,张树安、张田安两兄弟匆匆赶去,用镜头定格下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影像!至于北斗书院在朝阳巷的具体运行情况,那些尘封的细节,就只能寄望于未来成立的北斗书院文化研究社,去深入挖掘、细致考证了。
北斗书院是曾经浮梁北乡的文脉,也是浮梁北乡茶瓷商贸的商脉,是浮梁北乡曾经的精神文化家园。其兴教读书求学之风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清乾隆版《浮梁县志》主编凌汝绵在《昌江杂咏》所言“十户人家九读书”。近年来,峙滩镇及峙滩流口村率先倡励学之风,兴田接着跟进,经公桥港口有位叫计雄杰的老板,每年个人拿出钱奖励全镇考上大学的学子。浮北读书之风越来越浓烈,浮北人才辈出如大小北河源源不息!